
作者:凯利·兰伯特(Kelly Lambert)
伦道夫·梅肯学院(Randolph Macon College)的一名神经学教授,著有《实验室小白鼠的编年史:一位神经学家从地球上最成功的哺乳动物那里发现的生命奥秘》
翻译:王湛
我永远忘不了12年前的那一天,那是在12月,我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场家庭假日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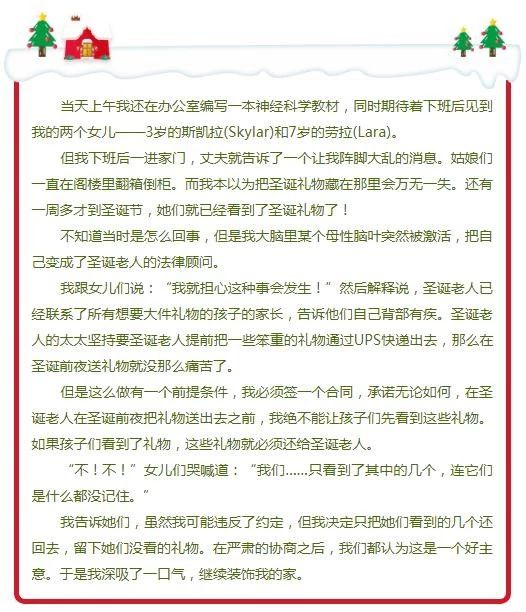
我不仅是一个母亲,还是一名行为神经学家、一个教授,而且总的来说是一个性格严肃、注重事实的人。那么,我刚刚到底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要编出这个不可信的故事,不顾一切地想要保护我的女儿们对圣诞老人的幻想,而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她们真相?
尽管表面上看,我似乎是把我所受的科学教育都抛诸脑后了,但事实远非如此。
尽管儿童生来就有完整的860亿个脑细胞或神经元,但在幼年时期,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相对稀疏。随着大脑的发育——神经元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微线延伸,在微小的沟回里出现了神经化学物质——孩子们慢慢学到了客观世界的法则,了解了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
最终,他们知道了驯鹿不会飞,圣诞老人也不会在一天晚上来到每个小朋友家,即使他真的来了,也不可能吃掉所有饼干。随着反映真实世界的成熟的神经回路变得强大起来,相信幻想的感觉就会慢慢消失。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不会彻底失去原先的这些思维方式,因为大脑似乎拥有一种神经时间旅行的机制。我所说的神经时间旅行机制并不单指在成年之后拥有曾经相信过圣诞老人的温暖记忆。


心理时间之旅的概念告诉我,努力让女儿们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是正确的。每年,我都让她们的大脑增加一次关于圣诞节的记忆,她们也会越来越容易地重新获得这种感受。
在我自己的童年,那么多年里我都会背诵着“圣诞节前夜快要到来”(’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闻着冷杉树的气味,然后满怀期待地入睡——那种期待,仿佛是可卡因成瘾者在盼望着吸到一生中最过瘾的一次。这些记忆已经成为我的大脑中关于假日的永恒记忆的一部分。
神经科学无意间还证实了圣诞节蕴含的更多智慧:
对假日的期待可以像收到真正的礼物一样令人兴奋。

如今,我是一个如此的务实人,以至于我的女儿们都开玩笑地叫我“骨头姐”(Bones)(Fox电视台的《识骨寻踪》里那个清心寡欲、社交能力低下的法医人类学家)。即便如此,因为我在大脑还能毫不费力地想象出驯鹿飞翔的景象时,强化了节日的记忆,所以每当我遇到到节日的景象、气味和声音时,仍然能产生圣诞节的神奇感受。
就像是巴甫洛夫(Pavlov)的流口水的狗,我的“圣诞情绪”是条件反射的结果,这些条件反射在我大脑的不同区域受到了巩固,适当的景象和气息的刺激,仍然能让我感到节日的兴奋。
因此,尽管我讲出那个圣诞老人后背不好的蹩脚故事时,正处在妈妈模式,而不是神经科学家的模式,但神经科学研究证实,努力确保我的女儿有一个唤起假日情感的途径,对她们成年后的大脑是有好处的。
我相信,这和儿童时期注射疫苗一样重要——它适用于所有孩子,无论他们记住的是圣诞节,还是别的什么庆典或传统。长大成人后,即使我不在她们身边了,圣诞老人的形象也会让我的女儿们,再一次像孩子那样看待这个世界,哪怕只是稍纵即逝的些许瞬间。
